大家都在用作弊的方式度过大学
ChatGPT 颠覆了整个学术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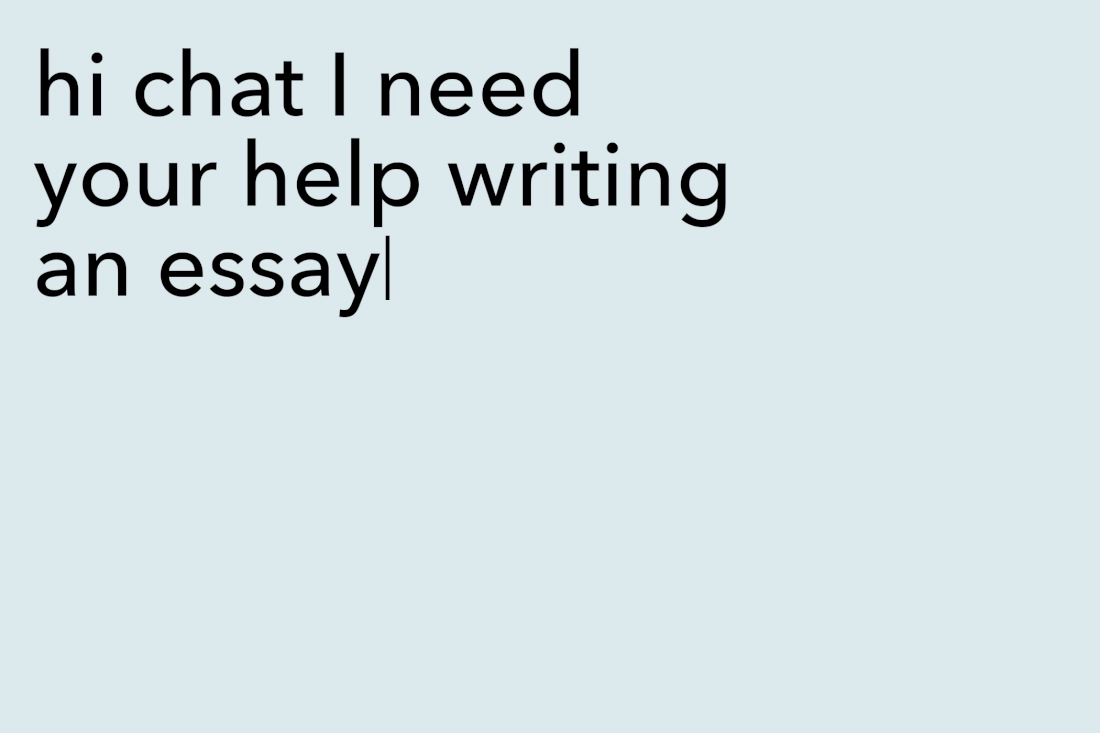 秋季入学的钟仁(音译)“罗伊”李踏进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几乎在每一项作业中都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作弊。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他在初级编程课上高度依赖 AI:“我基本就是把作业要求丢进 ChatGPT,然后把它吐出来的东西直接交上去。”他粗略估计,自己提交的每篇论文有 80% 都是 AI 写的。“最后的收尾是我自己完成的。我会插入我 20% 的想法和语气。”李最近对我说。
秋季入学的钟仁(音译)“罗伊”李踏进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几乎在每一项作业中都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作弊。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他在初级编程课上高度依赖 AI:“我基本就是把作业要求丢进 ChatGPT,然后把它吐出来的东西直接交上去。”他粗略估计,自己提交的每篇论文有 80% 都是 AI 写的。“最后的收尾是我自己完成的。我会插入我 20% 的想法和语气。”李最近对我说。
李在韩国出生,在亚特兰大郊区长大,父母经营着一间大学申请咨询公司。他表示,高中最后一年他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但由于毕业前的一次集体出游中偷溜出去玩,他受到了校方的处分,哈佛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录取。一年后,他申请了 26 所大学,但都没被录取。于是他先去社区大学读了一年,然后再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转学个人陈述,也就是把自己坎坷求学之路写成了创业雄心的寓言式故事,部分是在 ChatGPT 的帮助下完成的。)当他在大二的秋季正式入学后,他并不怎么担心学业或成绩。“大学里的大多数作业都没什么意义,”他说,“用 AI 就能很轻松地搞定,我压根没兴趣自己去做。”当其他新生还在为哥大严苛的通识核心课程发愁时,学校却宣称这些课程能够“开阔思维、改变人生”,但李用 AI 轻松地完成了大部分作业,几乎不怎么费力。当我问他为何大费周章进了一所常春藤名校,却把所有学习都交给机器人来做,他回答:“这是结识创业伙伴和未来伴侣的最好地方。”
到第一学期末,李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的一半。他在工学院认识了大三的尼尔·尚穆加姆(Neel Shanmugam),两人一起想出了各种创业点子:只面向哥大学生的约会应用、面向酒类经销商的销售工具,以及一个笔记应用。但这些项目都没有成功。随后,李又想到另一个主意。身为程序员,他曾在 LeetCode 上耗费了大约 600 个小时,这个平台用来训练程序员在求职面试中应对各大科技公司的算法难题。李和许多年轻开发者一样,觉得这些算法题既枯燥又不太贴近实际编程工作。“纯属浪费时间。”他想,如果做个能在远程求职面试时屏蔽浏览器、暗地用 AI 的工具,让面试者蒙混过关岂不是更好?
2024 年 2 月,李和尚穆加姆推出了这样一个工具。他们的网站叫 Interview Coder,横幅标语是 “F*CK LEETCODE”。李还在 YouTube 上发了自己用这个工具作弊参加亚马逊实习面试的视频。(他其实被录取了,但最后放弃了。)一个月后,李被叫去哥大学术诚信办公室。在一次委员会的调查后,学校给了他纪律留校察看的处分,原因是“宣传作弊工具的链接”和“提供给学生使用该工具并自行决定如何使用的相关信息”,这是委员会报告中的原话。
李觉得哥大此举荒谬,因为哥大与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有合作关系,却因此处罚他。他提到,哥大和许多大学的政策都类似:学生如果要用 AI,除非老师在某门课或某次作业上明确允许,否则就算违规。可李说,在哥大,他还没见过谁不用 AI 作弊。需要说明的是,李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们离所有人都不认为用 AI 写作业是作弊的时代,恐怕只有几个月或者几年不到的时间了。”
2023 年 1 月,在 OpenAI 正式推出 ChatGPT 仅仅两个月后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 名大学生里有将近 90% 用这款聊天机器人做过作业。在它面世的第一年,ChatGPT 的月访问量几乎每个月都在稳定增长,直到 2023 年 6 月学校放暑假才有所下降。(那并非反常:2024 年暑假访问量也再次下滑。)教授和助教们越来越多地看见学生交上来的论文充斥着笨拙的机器人语句,虽然语法完美,但不像大学生写的,甚至不像人写的。两年半后,无论是在大型州立大学还是常春藤,在新英格兰的文理学院或海外大学,或者法学院和社区大学,所有地方的学生都在用 AI 来减轻学业压力。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ChatGPT、谷歌 Gemini、Anthropic 的 Claude、微软的 Copilot 等——能帮他们记笔记、做学习提纲和模拟考题,能概括小说或教科书的内容,能帮忙头脑风暴、拟大纲甚至直接写论文。理工科的学生则用 AI 来自动化研究、分析数据,轻松搞定繁琐的编程和调试作业。正如犹他州一位学生在给自己拍的 TikTok 视频配文:“上大学就看你会不会用 ChatGPT 了。”视频里,她正把一整章名为《种族灭绝与大规模暴行》的教材复制粘贴到 ChatGPT 里。
加拿大安大略省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大一的莎拉(化名)说,她第一次用 ChatGPT 作弊是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学期。“当时我先熟悉了这个聊天机器人,然后所有课都用它:土著研究、法律、英语,还有一门叫‘绿色产业’的类似嬉皮农耕课。”她说,“我的成绩超好,它改变了我的人生。”今年秋季一进大学,她就继续使用 AI。有什么理由不用呢?她几乎每次上课都能看到别的学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 ChatGPT。到学期末,她开始觉得自己也许已经对这个网站上瘾了。她本来就觉得自己离不开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和 Reddit(她的用户名是 “maybeimnotsmart”)。她说:“我在 TikTok 上可以刷几个小时,直到眼睛疼到无法集中精力做作业。而 ChatGPT 可以让我在两小时内搞定原本需要 12 小时写的论文。”
有些老师想过对策,比如让学生用笔在蓝本(Blue Books)上写,或者改成口头考试。圣克拉拉大学的科技伦理学者布赖恩·帕特里克·格林(Brian Patrick Green)在第一次尝试 ChatGPT 后,就立刻停止了布置论文作业。但不到三个月后,他教了门叫“伦理与人工智能”的课,想着或许可以布置一个低要求的阅读感想作业——毕竟不会有人傻到用 AI 写这种带有个人感受的文章吧?结果还是有学生交上了带有机械语言和古怪表述的论文,格林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的。远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则发现学生在“伦理与技术”课程的第一次作业里用了 AI,当时的题目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你希望从这门课里收获什么”。
并不是说作弊是新鲜事。可现在,正如一位学生所说,“作弊的天花板被彻底掀开了”。面对这样一种让作业变得无比轻松又似乎不会被抓包的工具,谁能抵抗?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教授、诗人和哲学家特洛伊·乔利莫尔(Troy Jollimore)已经改了近两年 AI 写的论文,他很担忧。“未来会有大量学生大学毕业,进到职场,可他们基本不识字,”他说,“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文盲,也包括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本国文化——更别说其他文化——也一无所知。”事实上,考虑到大学不过四年,这种未来可能很快就会来到。毕竟,目前大约有一半的在校本科生在大学期间从没经历过没有 AI 的生活。“我们正在面对这样一代学生,他们的学习过程很可能已经被严重破坏了,”格林说,“就像一条捷径切断了正常的学习机制,而且发展迅猛。”
在 OpenAI 发布 ChatGPT 之前,作弊已然到了某种顶峰。那时,许多学生都从高中网络授课过渡到大学,习惯了无人监督,还有人用过 Chegg 和 Course Hero 之类的工具。这些公司号称是教材和课程资源的在线图书馆,但实际就是万能作弊帮手。比如 Chegg 每月 15.95 美元的订阅费,就能让用户随时随地发题过去,30 分钟内就能拿到来自全球 15 万名拥有高学历的专家(主要在印度)的答案。ChatGPT 一上线,学生们自然容易接受一个更快更强大的工具。
学校管理者却无计可施。要禁止 ChatGPT 完全不现实,多数学校只能采取临时措施,交由教授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学生用 AI。有些大学表示欢迎,与开发者合作,为学生注册课程推出聊天机器人,或开设专门针对生成式 AI 的课程、证书项目、甚至本科专业。但在实际管理上却很棘手:到底允许学生获得多少 AI 帮助?能否允许学生与 AI 互动获取灵感,但不准它代笔写具体段落?
如今,教授常在课程大纲中附上自己的 AI 政策——比如只要像引用其他文献一样注明使用过 AI,就可以使用;或者可以用 AI 进行思路拓展,但不能让它写具体句子;或者要求学生提交与聊天机器人的完整对话记录。但学生往往把这些说法当作“参考建议”而不是铁则。有时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问 AI 来润色草稿或查找文献算不算违规。在一所顶尖大学读大一金融专业的温迪(化名)告诉我,她反对使用 AI,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是反对直接复制粘贴,反对作弊、抄袭,这些都违反学生手册。”可随后她一步步详细描述了前不久某个周五早上八点,她如何打开一个 AI 平台,帮她赶在两小时内写出一篇 4-5 页的论文。
温迪每次写论文都要用到 AI(也就是说,每次写论文她都会用),总结了三步走。第一步:她会先告诉 AI:“我是一名大一学生,我正在上某某英语课。”否则,温迪说,“AI 给出来的写作风格会很高级,很复杂,但你不想要那种。”第二步:温迪会给出一些课程背景,然后把教授的具体作业要求贴进去。第三步:她对 AI 说,“根据这个题目,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提纲,或一种写作思路,让我按照这个结构写论文?”接着,AI 就会给她罗列出大纲、引言、主题句、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等等。偶尔,温迪还会让 AI 列出支持或反对某个观点的关键论据:“我不太擅长组织结构,这样就特别好,可以跟着写。”
当 AI 输出了一个大纲和要点,温迪就把它补充完整。结果她在 10:17 交了五页纸,虽然比截止时间晚了 17 分钟,但还算凑合。我问她作业得了多少分,她说成绩不错。“我其实很喜欢写作,”她带着一种对高中英语课的怀念说,“那是我最后一次不用 AI 写论文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去策划一篇论文蛮有意思的,你要动脑子想,这段写什么好,我的中心论点要怎么组织?”可相比之下,她更想要好成绩。“要是用 ChatGPT 写论文,它会直接告诉你怎么写,你就不用怎么费脑了。”
我让温迪把她那篇论文给我看,结果打开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她的题目竟是“批判教学法”,这是由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倡导的教育哲学,探讨社会与政治力量对学习和课堂互动的影响。她的开头写道:“到底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后面她又写到学习能够使我们“真正具备人性”。等我再和她聊到这个话题,问她是否觉得用 AI 写这样一篇本该批判教育本质的论文很讽刺,她有点不知所措。“我每天都用 AI,”她说,“我也承认它会夺走一些批判性思考,但——现在我们已经这么依赖它,真的很难想象没有它怎么办。”
几乎所有教写作的教授都跟我说,他们看得出来哪些论文是学生用 AI 写的。往往语言过于平滑,句式扁平;有时则干脆死板生硬。整篇文章看起来观点太平衡——好像主论点和反论点都一样充分。常见的词眼里会频繁出现类似“多层次视角(multifaceted)”“语境(context)”之类。有时更明显,去年有老师收到一篇开头是“作为一款 AI,本人已被编程……”的文章。但更多时候就没这么明显,导致抓住 AI 抄袭并不容易。于是有教授想出“特洛伊木马”方法:在作业指令里插入一些奇怪词句,并把它们用白色字体隐形在段落之间。(原理是如果学生直接复制到 ChatGPT,让它接着写,成品里就可能冒出一段莫名其妙的内容。)圣克拉拉大学有老师在作业里藏了个“broccoli(西兰花)”,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一位教授在 2023 年秋季布置作业时偷偷要求学生“提到芬兰”和“提到杜阿·利帕(Dua Lipa)”。有学生发现了圈套,在 TikTok 上提醒同学:“它确实有时会起作用,”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的乔利莫尔教授说,“我也用过‘亚里士多德会怎样回答’这种,本班根本没学过亚里士多德。或者我写些完全荒谬的东西,结果他们交上来的论文里也有,我就知道他们根本没看自己写的东西。”
不过,教授们也明白,即使他们感觉自己能分辨出哪些论文是 AI 写的,但实际上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擅长识别。2024 年 6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在英国某大学用虚拟学生档案夹带了 100% AI 写的论文交给教授评分,结果教授没能识别出 97% 的 AI 论文。更何况自 ChatGPT 上线后,AI 写的东西越来越像人类。正因如此,不少大学引入了 Turnitin 等 AI 检测工具来识别论文是否是 AI 生成的。检测结果通常会给出一个“可能是 AI”占比的分数,学生之间甚至传言某些教授只要超过 25% 就算学术不端。但我问了不少不同类型院校(大型州立、小型私立、顶尖名校等)的教授,他们没人承认把某个分数阈值当成判定标准。大多数教授也认为 AI 检测软件并不可靠。其实不同工具的准确率差别很大,互相矛盾的结论不少。有些说自己的误判率低于 1%,可也有研究显示它们对神经多样性学生或母语非英文学生的文章尤其容易误判。Turnitin 的首席产品官安妮·切奇泰利(Annie Chechitelli)告诉我,他们的产品作了倾向性调校,宁可漏判也不能错判学生,从而避免无辜者被指控。我把温迪的那篇论文扔给免费的 ZeroGPT 去检测,结果显示 “11.74% 是 AI 生成”,看起来挺低,而实际上至少论文的中心论点是 AI 提供的。然后我把《创世记》里的一段文本也给 ZeroGPT 测试,结果它显示“93.33% 是 AI 写的”。
事实上,有许多简单方法能躲过教授和检测工具。最直接就是让 AI 写完后自己手动重新润色,或者让 AI 再次改成“更像人写的”“加些错别字”。TikTok 上有学生分享说,她喜欢用的提示词是“模仿一个有点笨的大一学生写出来的论文”。还有人让 AI 洗稿——先用一个 AI 写,再用另一个 AI 改,然后再用另一个 AI 改第三遍,很多检测器就被搅糊涂了。“他们非常懂得操纵系统。先在 ChatGPT 输入指令,再把输出丢到另一个 AI 系统,最后再进第三个 AI 系统。这样再用 AI 检测器测,AI 生成的占比会一次比一次低。”就读斯坦福大学大二的埃里克(化名)说。
大多数教授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想要通过单独查处来遏制 AI 大范围滥用几乎不可能,除非对教育体系做出彻底变革,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作弊与心理健康、自我认同、睡眠不足、焦虑、抑郁以及归属感有关,”斯坦福大学高级讲师、著名学生学习研究者丹妮丝·波普(Denise Pope)说。
许多老师现在都感到一种无力感。去年秋天,萨姆·威廉姆斯(Sam Williams)在爱荷华大学当助教,给一门“音乐与社会变革”的写作密集型课程批改作业。课程的官方规定是不允许用 AI。他在批改第一次作业——“写一篇关于你个人音乐品味的文章”——时还觉得挺开心。但到第二次作业,关于新奥尔良爵士乐早期(1890-1920),明显很多学生的写作风格突然变了,还出现很多荒谬的事实错误。好几篇论文专门谈到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可猫王明明 1935 年才出生。“我当时对全班说,‘别用 AI。但如果你非要作弊,也要动点脑子,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威廉姆斯回忆说。
威廉姆斯知道,这些选修课的学生大多不打算成为作家,他只是觉得从空白页到写出几页成文,这个过程本身是一种努力的磨炼。但现在看上去,他们全程都在依赖 AI。“他们用 AI 是因为那是能让写论文这件事变得简单的捷径。我能理解,毕竟我自己当学生时也不喜欢写论文。”他感慨,“可这样一来,每逢遇到点困难,这些学生不再试着解决和成长,而是退回到能让他们轻松应付的东西。”
到 11 月时,威廉姆斯估计至少一半学生在用 AI 写论文。尝试惩处的努力几乎无效。AI 检测工具靠不住,而这门课的教授也不让他给那些明显 AI 痕迹的论文判零分。“每次我和教授提这事,他都觉得 ChatGPT 没那么厉害,系里的态度也是‘这事情不好界定’,我们也没法证明他们用了 AI。”威廉姆斯说,“教授让我按照‘如果那是认真写的论文,会打多少分’去打分,所以我等于在考察他们用 ChatGPT 的能力。”
这种“假装那是学生认真写的”政策让威廉姆斯的评分体系完全乱套。如果一篇显然是 AI 写的“好论文”可以得到 B,那么某个真的自己写、但写得“几乎看不下去”的学生又该给什么分?这种纠结让威廉姆斯对教育本身也失望透顶。到学期结束时,他对研究生学习再也没兴趣,干脆退学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代,新时期,而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事。”他说。
教了二十多年写作的乔利莫尔教授,如今确信人文学科,尤其是写作课程,正在变成类似手工编篮那样的“技艺兴趣课”。“每次我和同事们聊起这事,大家都会提到同一个话题:退休。‘我啥时候能退休?我啥时候能离开?’这几乎成了共同心声。”他说,“这不是我们当初签约来做的工作。”威廉姆斯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形容,AI 带来的冲击简直是一次彻底的存在主义危机。“学生们也觉得系统本身已经坏掉了,没有继续努力的意义。这些作业最初想传递的价值也许已经丧失,或者并没有传递给他们。”
他还担心,如果对 18 岁的年轻人放任自流,长期后果会怎样?他们缺乏刻意练习,不去认真写作和思考,职场的“软技能”差距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如果学生依赖 AI 度过所有学业,那么到了职场,他们能带来什么真正的能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讲师拉克什亚·贾恩(Lakshya Jain)就常对学生说:“如果你交上来的作品全是 AI 做的,那你其实就是给 AI 当人形助理而已,这样人家公司为什么要留你?你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地方。”这并非空想:有家科技研究公司的 COO 就曾问贾恩,“那我为什么还需要程序员?”
大学从来就不全是“陶冶情操”的场所,在高昂的学费和“赢者通吃”的经济现实面前,不少人早已把上大学当作交易——是为了毕业后找到工作。(德勤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一半多点的大学毕业生觉得自己花几万美元一年的学费是值得的,而职业学校毕业生有 76% 认为合算。)可以说,AI 极快且轻易地展现了能完成大学水平学术工作的事实,只不过是让我们看清了大学体系内部早已腐败的核心。“既然社会把上学当成谋求高薪与社会地位的手段,那怎么指望学生懂得教育的真正意义?更糟的是,社会甚至可能认为教育毫无价值,把它看成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乔利莫尔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教授也不是全部清白:现在已经出现不少 AI 工具,可以帮助老师对学生作业进行批改,给出 AI 生成的反馈。这就意味着,很可能出现 AI 给 AI 写的论文评分的局面——到头来就只剩下两个机器人(也可能只是同一个机器人)自说自话。
要想知道这些对学生大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得等几年才看得清。有些早期研究表明,学生把认知任务交给聊天机器人后,会让他们的记忆力、问题解决和创造力等能力下降。过去一年里,多个研究项目也把使用 AI 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的退化联系起来;其中有一项发现,越年轻的人群受影响越明显。2023 年 2 月,微软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越依赖生成式 AI,就越倾向于减少批判性思考的投入。如果再想到社交媒体对 Z 世代辨别真伪能力带来的冲击,这一切就更加让人担忧。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早在生成式 AI 出现前,人类的 IQ 早已显示出类似端倪。“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的是自 1930 年代以来,每一代人的 IQ 测试平均分都在上升,可这个趋势在 2006 年之后开始放缓,甚至逆转。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曾对《卫报》表示:“在这个生成式 AI 的时代,人们最担心的或许不是它会不会危及人类的创造力和智力,而是它已经在这么做了。”
不少学生也有此顾虑,却找不到办法戒掉让他们生活轻松无比的 AI。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丹尼尔(化名)告诉我,他还清晰记得第一次用 ChatGPT 的场景。他当时冲到高中计算机老师的办公室,打开 Chromebook 给他看:“哥们儿你一定得看看这个!”他说,“我爸回忆起当年史蒂夫·乔布斯发布 iPhone 的演示,觉得那是大事。这对我来说,就像我未来可能天天用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
AI 让丹尼尔更好奇,他喜欢有疑问就能迅速得到详尽解答。但当他用 AI 写作业时,他常会想:如果我花时间去真正学会它,而不是直接问 AI,那我会不会学到更多?可回到现实,他依旧让 AI 帮他润色论文、写开头几段、处理编程课的繁琐部分,总之能偷多少懒就偷多少。有时候,他知道自己这算学术违规,但多数时候他觉得是在灰色地带。“如果把 AI 当成家教,你说这算作弊吗?可如果那位‘家教’开始替你写句子呢?”他说。
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大一的马克(化名)最近跟一个朋友提起自己在某次编程作业中,比平时更多地依赖了 ChatGPT,朋友回了句似乎能安慰人的比喻:“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个包工头,使用各种电动工具建房子,但没有你,人家就不会有这栋房。”马克却说:“问题是,这房子到底还是不是我盖的?”我问丹尼尔一个假设场景,想从侧面了解他如何界定“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假如你发现你的伴侣给你发了一首 AI 生成的诗,你会生气吗?他想了想:“我猜要看你重视这首诗本身,还是更重视对方亲手创作的过程?过去写情书两者兼顾,现在就很难了。”他说,现实中自己会写手写便条,但在此之前,往往会先让 ChatGPT 帮忙润色一下。
杜克大学教授奥林·斯塔恩(Orin Starn)在一篇名为《我对抗 AI 作弊的失败之战》的专栏里写过这样一句话:“语言是思想之母,而非思想的仆人。”但不光是写作能培养批判性思维,数学学习也是训练系统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就算你将来用不到代数、三角函数或微积分,但你会运用那些技能去辨别逻辑是否通顺,”德州农工大学副教务长迈克尔·约翰逊说。青少年需要在有结构的环境里应对困难,不管是学代数还是做家务,才能建立自我效能感和责任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就强调孩子学会面对艰难任务是多么重要,而技术正在让所有事情变得轻而易举。OpenAI 的 CEO 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曾多次淡化人们对学生用 AI 的担忧,称 ChatGPT 只是“文字计算器”,作弊的定义需要升级。“传统写论文的方式今后肯定不再是主流了,”他这样说过——他本人也是个从斯坦福退学的人。但在 2023 年美国参议院科技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也表示自己担心:“我担心随着模型变得越来越强,用户的辨别思维会越来越弱。”OpenAI 对大学生市场可以说一点不避讳。2023 年期末考试期间,它曾让大学生免费使用本来需要 20 美元月费的 ChatGPT Plus(2024 年夏天一样搞过)。它也认为学生和老师只要学会“合理使用 AI”就行,比如它向高校提供 ChatGPT Edu 专门产品,来教大家合理运用。
李在 3 月底因为在 X(原推特)上公开了那次校方听证会的细节,被哥大停学。他表示没打算回学校,也不想进大厂工作。他说,当初公开演示远程面试作弊的意义在于推动科技行业尽快调整,就像 AI 正在逼迫高等教育改变一样。“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促使人类回头想想,‘究竟什么工作是有意义的?’也许在 17、18 世纪时就有人抱怨机器取代铁匠,但现在我们早就习惯了,学打铁没什么用了。”
如今,李早已不玩面试作弊那一套了。今年 4 月,他和尚穆加姆发布了名为 Cluely 的新工具,能扫描用户电脑屏幕并监听音频,实时为用户提供 AI 反馈和答案,而无需输入任何提示语。他们在产品宣言里写道:“我们开发 Cluely,是让你再也不用独自思考。”他们把这款工具称作隐藏在操作系统里的超级伴随 AI。李为 Cluely 再次策划了一次高调上市,为此拍了一个花 14 万美元制作的广告短片:剧情里,他是一个年轻的软件工程师,戴着装有 Cluely 的眼镜,与一个比他年长的女性约会。当气氛变尴尬时,Cluely 建议李“夸夸她的艺术创作”,并给了一条现成的说辞。李照着念:“我在你资料里看到了你画郁金香的作品。你是我见过最棒的女孩。”结果这救了全场。
发布 Cluely 之前,李和尚穆加姆已从投资者那里融到 530 万美元,使他们得以招聘两名程序员(都是李在社区大学认识的朋友,无需面试或 LeetCode),并搬到旧金山。我们通话那天是 Cluely 推出的几天后,他正在房产中介办公室,即将拿到新办公场所的钥匙。他边和我聊,边在电脑上运行 Cluely。虽然 Cluely 目前还不能通过眼镜实时投放答案,但李想要的是将来能把它装进随身可穿戴设备,让它看见、听见、并及时回应你周围的一切。“再往后,就是直接在你大脑里了,”李语气平静地说。至少现在,他很希望人们用 Cluely 来扩大对教育的“攻城略地”:“我们的目标是数字 LSAT、数字 GRE,以及所有网课作业、小测验、考试,通通都能用 Cluely 作弊。”他说,“它可以让你在几乎所有考试上都能作弊。”